展示中作品多為二次元同人衍生、含有男同元素(成人向)
與渋及到的原作(者)或其他製作者們無任何関係。
請勿以任何形式未授權轉載或再次加工、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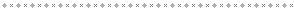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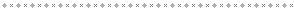
×
[PR]上記の広告は3ヶ月以上新規記事投稿のないブログに表示されています。新しい記事を書く事で広告が消えます。
想忘記所有 那是自欺欺人的戲言。
雲雀死後,我帶著他回到久違的並盛町。
二月雪雖然已不再下,但天氣絲毫沒有轉暖的跡象。依舊有些潮濕的空氣會加速屍體的腐爛程度,我們要快些將他下葬。陰宅在這裡幷不盛行,人們提倡火葬。但這種屍骨無存的結局,雲雀定是不會喜歡,我便吩咐下屬到郊區找片寧靜的地方直接搭個粗俗的墳頭也行。
晚上會忍不住企圖潛入醫院瞧眼暫時被寄存在太平間的雲雀,思念這種東西也會呼之欲出頗有力度折磨我。不要讓自己閒著,是我唯一可以稍微緩和焦灼情緒的良藥,但在這片毫無留戀的地方又有何處可徘徊消遣。
叼著煙游走于幷盛與黑曜中學之間,原來這兩個地方一直以來都不算遠。十多年沒有再回到這裏,記憶裝置早已生銹到發動不能。只記得可代表日本的櫻樹散瓣,在春分後的歲月裏漫天無邊的飄著、墜落在一襲黑衣的雲雀肩頭。
那時候連微笑都不知爲何物的盛氣淩人,我們固執殘暴的個性已然不見蹤跡。相似的人走在一起價值何在?忍痛磨合的結果是我們都幷不擁有對方任何。如若說定是佔有了你的某個事物,那也許是我一直爭取與你獨處的批量時間。
現在你的時間靜止了,而將我席捲於裂紋縫隙中動彈不得。
這就是所謂的永恆?
陰陽相隔實在是無聊且費力的遊戲。
上篇 追憶的粒子
一旦到了夏季,生活便會異常紊亂:
如果可以撐得過去,我連一頓飯都懶得吃。
勉強在彭格列總部屁大點的小餐廳裏混幾塊乾巴巴的麵包片、抹上油膩的黃油乳酪、配上一份小杯可哥沾了再吃,大可以平復肚子可憐的哀號聲響。
執行任務回來,醫療隊人員無頭蒼蠅般慌亂搶救我背回早已僵硬的屍體,卻始終無法阻止一個生命的離去。犬杵在停屍間門口任憑你挪動他都不肯退讓一步。
「別這樣,千種已經死了。你站在門口會擋到其他人的。」 我儘量將語氣放平緩。
「…骸大人…現在這種情況至少縱容我一下吧?當時耍帥都不行?」
「……」 我講不出任何安慰的話,只好官方口腔:
「耍完了就快回去給我換件乾淨衣服再來,然後我們一起吃飯。」
他像是沒有聽到,機械的點頭回應我。
走廊內擦肩而過的行人紛紛投來同情的目光。
我知道他們在盯著任憑我堂而皇之掛在眼下的濃重黑眼圈、聳立鼓囊的眼袋。
這是我可以獻給親愛的千種唯一的悼念禮。
「骸,你走起路來怎麼像吸毒?你有認真吃飯嗎?」
親愛的彭格列看住我歪斜踉蹌推開厚重的實木宅子大門,滿是擔心的語氣。
我回給他佯裝出的燦爛笑容,猛然間精神充沛。 「我怕熱,吃不下飯呢~晚上屋子裏蚊子又凶得很,我被折磨到困極竟然會失眠啦。」
「你黑眼圈重的很呢……」 綱吉總是一副母親的溫柔,害的我心虛。
「…沒事沒事,夏天作祟夏天作…」
果真會有頭暈目眩的昏厥,我急忙扶住手邊的水泥砌樑柱。
眼前映射灰刷刷分裂成幾份在晃,嘔吐感倍增。
「就這樣,沒事我就先回去了首領。」
綱吉仍然眼神饒不過的釘在我身上,感覺得到背後火辣辣。 我再回頭想安慰他幾句,結果反倒是被他瞳中一汪汪憐憫給驚嚇到。
「骸……」
「沒事啦~」 我急忙帶上門出去。
「……等下…」
首領你再叫我小心我「哇」一下子真的吐出來給你看噢。
經新上崗的司機再一折騰,我真的連爬出後座的力氣都沒有了。
這師傅看來是緊張、心事多重的人,又覺為我開車是伴君如伴虎麼?一路上開車小心翼翼卻又掌握不好力度收放油門,加速度跌宕的很。時快時慢的幾下子極速剎車,致使我徹底將肚子裏最後零星存量可供消化的晚餐都吐了出來。
從後視鏡我看到自己一張綠油油的臉。
到家已是深夜了。
翻來覆去在包內找不到關鍵時刻最喜歡和我作對的鑰匙串,我雙腳無力支撐著重擔身體,一下子癱軟在房門口像個被老婆逐出家門的醉鬼。摸索著手機看了下時間……哦天,所謂的生日就是在這忙碌中完全被甩到外太空去了,再不到二十分鐘時間、日曆又將翻去到十日,我便沒時間故作煽情狀少女情懷的掏出家裏幾本單薄的相冊翻翻看,懷念下曾經的懵懂青春(好噁心)。
總之,先打開這門比較重要。
又開始徒勞翻找不起眼的鑰匙…
「六道骸?」
我仰頭瞄出暗夜流螢閃爍幽光的鳳眼。
我與這雙眸的主人已經有半年沒有見面了。
雲雀,你沒事晃到我這裡做什麽…幹。
真是倒黴催死了,我這狼狽樣恰巧被這毒舌瞧見了。
與其等下會被嘲笑到大打出手,還不如我一口咬舌自盡的好。
不過,恰好終於在夾層翻到鑰匙的同時,我嗅到甜食的味道。
眼神不由自主被吸引過去盡數聚焦在他右手狀似禮品盒的什麽,還有蠻有狗血氣氛效果的一小束象徵性群聚的玫瑰——但卻是黃色的?!
我怒火開始蔓延。
再瞧他臉上表情,就是一副「感動吧讓你感動死了吧算了就讓你感動一次吧瞧我多好」的自大高傲神態。像是小學生趁著父母外出上班時蹩腳的整理房間順便做了一頓難以下嚥的晚餐、翹首以盼等著歸來的家長必定會表揚自己同時附贈些許額外零用錢的白癡狀。
但心仿佛被看透一般的,他掠過我因驚訝而僵硬幾秒手指間捏著的鑰匙,俐落的打開。
順便用最令我厭惡的相撲經典擁抱姿勢完全談不上絲毫雅觀的將我拖拽進了房間。
雖然雙腿在莫名其妙提醒著我快跑,但爲什麽……
竟然會忍不住心酸的體味到一種被珍視的痛。
你不是在日本麼。
蜷在沙發裏,我依舊不太舒服的與胃痛抗爭。雲雀今天八成是被某個人格搶先利用了,且此人格叫做「恭子」,性格特徵是少女粉紅泡泡,稍有撒嬌性質的細膩女性…
天,我是因為身體太過虛弱才胡思亂想起來了麽…
但看著他正吃力點著輕易就會熄滅的兩根數字蠟燭,我完全找不到可以吐槽的基點。
「我說……」
「終於搞定了。」 他一擊掌瞬間嚇飛我滿載的困意。
雲雀讓開身體,我才瞧得清明晃晃的兩處細小火焰,有些煙火效果著灼燒。
只是數字看著惹人生氣,竟然是「六」和「九」。
雲雀你不知道蛋糕上插蠟燭的話,至少是與年齡相同的數字吧…
我忍不住笑出來。火焰被我噴散出的氣息震蕩一顫顫,連同抖動著還有黑漆漆客廳內被映照在墻的雙人巨型黑影,以及我稍難再控制得當的心情。
再看一直背對著我的他,眼神幷沒有如預期的對上我些許期待。只是寂靜的,從我方向只瞥到他面部後側一路鈍下的硬朗綫條,難預測到是以什麽表情再瞧著蛋糕上亂寫的義大利語——「生日快樂」
倒是很像是他的字體。
「你從不記自己生日。」 他突然幽幽的講。或許也是我的幻聽。
我沒來由的心臟酥麻感迫使自己快些結束琢磨不透的幻影。
蠟燭燃著極迅速,不容我貪戀那刺眼的火光。蛋糕的奶香又引誘人會醉,我耷拉在雲雀的肩膀上。說不上是否懷揣著欲勾引之嫌,我喃喃的耳語講給他。
「謝謝了。」 這三個字我卻講的甭提多麼矯情。
他沒動,我只一個人緩緩向蠟燭吹出一口寒氣。
房間瞬間伸手不見五指的黑。
總有什麽在眼睛還未適應這突如其來的暗夜之前,與過往流動速度搭不上節拍。
胸腔滿溢一種濃度密度逐漸增強的氣體,鼓囊塞進憑空構築的中空的墻裏。
總難免會遭遇不同尋常的情緒起伏,其實我從未想要隱藏這些。
長久以來和雲雀都體味不到的酸澀,在今晚竟彙聚濃縮成雙份寂寞。
我聽得到面前這個男人心裏稍有些僵硬有所保留的悲慟,連同我的一起。
逐漸占領著我們之間本就狹窄的甬道,直至呼吸困難。
「開燈去。」
我將身體砸回沙發依靠著,賴賴的口氣支使他。
他沒聽我話——當然我也想到了,這種氣氛下他鐵定是要順水推舟做些什麽。
未來得及被我嗅到他足夠紊亂鼻息時,他就已經迅速轉身撲上來。順著我身體線條熟練遊走著,駕輕就熟解開曾經被他列為我身上難纏配件首位的繁瑣腰帶,冰涼的手指直接毫不客氣爬進我內褲裏面翻攪。
「我說雲雀大人,你今晚有點激動…」
他另一隻手卻生疏幷尷尬意味十足的解不開我襯衫上幾顆頑固紐扣,我看戲似的打趣說。
「…信不信我把你衣服撕爛?」 看不見那張獨占欲極強死要面子的撲克臉,我憑空想象下他窘迫卻不肯服輸的面癱樣。 「你隨便撕,臥室衣櫃裏這件樣式的還有三十多件,你盡可以撕個夠~」
「買那麼多?!…故意的吧!」 他一猛力扯開,那幾顆可憐的扣子不知蹦到角落哪裏去。
我抵抗著他過分靈巧的舌頭滑動在胸口。 「…恩…衣服是無辜的……」
從沙發翻滾下來跌在硬邦邦的實木地上,雲雀已把我們兩人全脫的一絲不掛。
排山倒海的湧動快感在腦內飈升,只有在做愛的時候才稍微可以感覺到他有點體溫。
要問是否真實存在這個軀體的,其實應該是我。
然而雲雀更像是死屍被還魂似的操縱,讓我尋不到根源蹤跡。
連同他的背景,過往。都不是一個他人的講述就可以瞭解的到。
「……慢、慢點…」
「…恩…」 嘴上敷衍的應和,動作卻絲毫不肯減少力度…
我感覺自己手腳筋快被要他那股蠻力扯斷。
頭痛欲裂牽動著胸口憋悶與胃腸止不住的痙攣,我像是瀕死的魚逃脫著他反復堵上來的柔軟,找到間隙忙著大口呼吸氧氣。
被雲雀蹂躪成一團廢紙壓癟至不成形,卻樂於享受下體更抑制不住的一股衝動要發泄。
「…雲雀,快…快去了……」
「等、等下…」 這東西可以等的嗎?!
我內心叫苦連天,嘴上卻一句諷刺語句組不出來。
真他媽的熱啊…
他頗有蠻力的手拼命套弄著,我抵抗幾次不能,快要被摧殘到欲仙欲死地步。
拼盡全力回應著極速的韻律,環抱住雲雀的脖頸將他頭壓低貼在我胸前。
總感覺…這種做愛方式像是在締造合同一般的……
「……嘶…骸,別夾那麽緊…要斷了。」
「恩…唔…」
大腦已經處於當機狀態,完全接受內容不能。
這關鍵時刻你教我,我也做不來了。完全憑藉本能出牌,誰還管你…
一片空白映射閃過……咬緊牙關泄了出來。
換了陣地再戰,比發情期的狗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再反反復復幾個回合下來,我倆只剩下癱軟無力雙雙摔在鬆軟的床。
身下粘膩到筆墨不能形容,然而一點做清洗的力氣都沒有。回想前一天在外奔波勞累外加飲食睡眠規律混亂,我隨便抽了紙巾胡亂擦拭了下倒頭便要睡。
雲雀沒有如往常膩上來再縱欲過度的索求,我瞬間便進入了夢鄉。
但之後總覺得那晚如果沒有睡就好了。
那夜的夢中,我只是在不斷溫習著千種死去的零碎片段。
二十九歲的生日卻成為他的忌日,有種辛辣的諷刺感。
醒來的時候,雲雀已經搭上返回日本分部的航班。
雲雀所說的,嘗試著記住一些對於自己來說重要的日子,已成為一種潛移默化的習慣。
然而意料不到的是,在未來的某日他用更特殊的方式,逼迫我永久銘記了六月九號。
恐怕以後再難忘記了。
中篇 艱苦彩飾一夜的極色
三年前雲雀被派到日本做了某地方組織的頭目,屬於彭格列分部範疇內。
有機會回到喜歡的國度生活,這無疑是一件美差。塵封多年的幾件浴衣被他洗的幹乾淨凈整齊碼在行李箱裏,我好像隱約聽到他在洗手間裏一邊搓衣服一邊在哼歌。
臨走前的那晚我們背對背躺在床上,他睡得無比之安穩我卻一夜沒有合眼。好不容易熬到淩晨四點鬧鐘響了,我爬起來坐在床邊瞧著天還藍紫色滲透著些許的白抽煙發呆,直到身後傳來窸窣的聲響。
剛準備回頭,雲雀像隻八爪魚從背後突如其來的緊緊捲住我,隨即爪子不安分起來。
茫然的注視他睡眼惺忪的一張臉,我雖然沒有那個心情但也沒有意思要抵抗。任憑他總是低溫的手不客氣的掀開我才剛穿上的襯衫,獸性大發似的又要索求無度。
雲雀架著我的腿貼近我額頭的時候,他木訥的神情令我甚至覺得他只是在夢遊。然而在這血雨腥風裏毫無招架縱容他玩弄我踐踏我、在我身上留下血肉模糊的傷痛,卻是彼此最好的告別方式。
從此以後,我和雲雀的見面也從每日每夜可以相見親熱,改為一年最客觀只有兩次倉促的碰面。而屈指可數的幾次機會中,我們基本都是縮進停在飛機場地下停車室的小型吉普裏,在有限的時間內瘋狂做愛。車會被我們做到嘎吱響才停止,好奇探頭看過來的人又是一臉羞憤的躲開了。
替換的衣物是必不可少的。在之前身上的那件上面定是會沾滿淫穢的體液,分不清是我還是他的,粘稠著團成一灘灘。
封閉的狹小空間裏滿是奇特的溫存味道,我可以嗅著它坐在車裡直到天亮。
夏天某個夜晚我和朋友喝的爛醉,回來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淩晨。
掏出手機發現有雲雀的未接電話,我才意識到才剛翻頁的竟然是自己的生日。
這時候他們那邊應該是白天沒錯。
我有些抱歉的撥了回去。
「太吵了,沒聽到你的來電。」
「大半夜不睡覺去哪兒瘋了。」
「出去吃飯才回來的。」
「慶祝生日?」
「不是啊,只是參加朋友的婚禮而已。」
「……」
他沒有再講話,我以為是電話突然中斷,「喂」了一聲。
「你什麽時候有休假。」 他沒頭沒腦的問我。
我沒能聽出他話中的情緒,不經大腦的實話講:「我最近很忙呢。」
他反應了幾秒鐘才又說: 「是麼,那你忙著吧,我掛了。」
他果然立刻生氣了。
「喂!」
「……」 他沒有收線也不言語,我從沉默中聽到細微的喘氣聲。
這種獨有的距離增添了曖昧,也堆積了心中的某些衝動。
我的心緊了又緊。
「如果你回來的話會更好。」
「我也想回去。」 他迅速的回答了我。
我沒聽錯吧。
他的語調還在我耳內來回盤旋著,我意識到這不是開玩笑。
難道他也喝酒了麼…我們都是只有在醉酒之後才會彼此坦誠的人。
「我已經習慣了義大利的所有,」 他壓著嗓子,沉悶著說。 「現在走在街上都能感覺到,日本的一切和我如此的格格不入。」
「我早已不是並盛的人了…護照上的國籍寫著義大利,一身西裝、歐式車、刀叉飲食。」
「我是意國人,我不是日本人。」
「很矛盾是吧呵……」
聽筒那邊傳來細碎的雨聲。
那麼熱愛著祖國的男人是用如何的表情談著這些有些殘忍的現實呢…我靜靜的合上眼簾,寂靜中形成一張他終年積雪偶爾融化後一灘灘的水漬上滿是愁苦的臉。
可這一切不但沒有激發我的同情,反而令我興奮、一種幾近病態的征服快感。
孤高的浮雲居然也會有不能停靠的天空,被酒精麻痹的我竟然可以開心笑出來。
當我聽到他說「我是意國人。」
之後怎樣掛電話的我完全忘記了,第二天起來的時候甚至懷疑這通電話是發生在夢中的。可一旦閉上眼睛,醒著夢著都能溫習那張陌生的臉、帶著沒人見過的表情躺在我旁邊。夜深的時候所有都滅絕一般的沉靜,只有虛無的黑暗中絲絲作響的痛苦喘息我聽的清楚。
一遍又一遍,一波又一波。像無情席捲萬物的洪水傾瀉而入,沖刷我、淹沒我。
就這樣度過多少時日,某個白日裡萎靡的醒來時,床頭手機瘋狂作響。
雲雀恭彌真的回來了。
然而如果可以選擇,我並不希望是在這消毒水沾滿身體的急診室裏。
也不想見到健碩的他奄奄一息癱在病床上,維繫著最後一點對生命的眷戀。
所有的人都在,他們整齊劃一的轉頭打量因為宿醉一臉蠟黃的我。
倚在角落裏的犬投射來的火辣視線像是在嘲笑我,諷刺在千種死時我一邊勸著他、一邊擺出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可恨嘴臉。
生死離別我經曆的太多,所以即使見到雲雀的屍體我或許也不會有什麽心痛,但是這種自負心理在我看到房間中央躺著的他時相當不堪一擊,灰飛煙滅。
一點點向著反方向挪著步子,我退卻了…
「雲雀在羅馬幾場遭到了索菲亞家族的暗中埋伏。」
「他和敵人的正面交鋒應該是在中了暗毒之後才開始的,所以占了下風。」
你不是一拐就打飛一群人了麽廢物。
「檢查報告出來了。」
夏馬爾指著化驗單上大大小小摸不透含義的數值,面部肌肉不易察覺的抽動。
「可以確定雲守身體裏存在有致命性病毒,恐怕是解離性銀虹三型。」
在場所有人均露出困惑的神情。
我瞳孔瞬間伸延至最大值。
銀虹,我知道的…
小時候的記憶中,和犬、千種逃出的那所研究室裏有無數人體小白鼠當做這種病毒的試驗品,存活率根本就是零。
夏馬爾壓低聲音。
「簡單的說,就是一種寄生型病毒依附於人體器官表皮…」
「潛伏期只有兩個小時,之後身體內器官就會異常疼痛,並持續這種症狀將近一周時間後感染者即會斃命。這種病毒特典在於並不是一擊致死,而是緩緩折磨,像是啃噬葉片一般將人體內臟吃的乾淨,從內至外的掏空般的……」
「雲守感染者這種病毒已經有三天時間了。」
「已經沒有希望了嗎……」 身邊仍有人怯聲的問著。
「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可能。」
「現在還沒有可以抵抗這種病菌的病原體,所以根本是束手無策。」
「我想,儘量在這幾天內尋找方法,醫院方面就讓他們多拖延時間吧。」
「急救車到了,護送他去醫院接受傷口處理吧。」
人群一哄而上,七嘴八舌的聒噪擠滿狹小的空間。
鏡頭中唯一靜止的我,視線僵硬的移動到雲雀臉上。
參差不齊的傷痕蔓延著,直到鉆進襯衫領中。不用猜也可以確定他身上還分佈著多少刀疤搶眼…眼睛卻是安詳的閉合著,單從神情上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痛苦。
在手術室外靠著冰涼的座椅我睡過了醒、醒來了再睡過去。就這樣整整二十個小時後,那隻一直亮著的紅色燈光終於熄滅了。麻醉藥劑一過,雲雀蘇醒過來,我堵塞的胸口也像是摸爬滾打在泥沼裏被糊上厚重的泥巴、卻終於爬上了彼岸。
但是噩夢才剛剛開始。
因為注射鎮痛劑過於頻繁,藥已經失去它該有的效力。雲雀逐漸在體內形成了抗藥性,現在即使注射給他超過正常人用量的一倍也無濟於事,看著他因痛而扭曲的五官,我的內臟全部擁堵成一團形成一把梭,他的吶喊與掙紮一圈圈的緊緊纏繞上面。
繩子、甚至是鐵鏈都無法將他束縛在床上。
他在手術後醒來直到現在從未合眼過,我也一樣。
從醒來直到現在他沒有和我講一句話,我也一樣。
我將所有無關人等鎖在門外,用無休止的幻術一次次制止他企圖自虐或是逃脫。我壓在他身上化成一把枷鎖,他的汗他的淚他的血毫無保留的吐沫在我身上,像是一種神聖的儀式在遞交著什麽……
像是站在風卷浪濤暴雨傾盆也玩的船甲板上,我們彼此抱住一個看似安全的木桶。隨著船不受控制的傾斜與起伏,我隨著木桶左搖右擺,完全失去了本能控制的方向。
而我的所有細胞都在鼓動、悲慟……哀號。
「放開我!放手!混蛋!」 肩膀像是快被他洶湧襲擊的牙齒咬爛了…
我咬牙挨過一次次……疼痛反倒是令我清醒了不少。
像是比他還要煎熬似的,還要受控不住…無力挫敗感用力敲擊著我的淚腺,然而能做的還有什麽?除去我這麼親密、這麼緊的抱著你以外?
我死死按住抽搐的軀體,將雲雀踢蹬雙腳壓在胯下。
「殺了我…殺了我…」
他仿佛有些軟弱下來,像是乞求的口吻叫著: 「……骸…骸…」
我整個心翻來覆去的在痛…
一個人負責掙紮,一個人負責桎梏。叮叮咣咣身體跌撞在某處的巨大迴響,我們像是正在激烈做愛的戀人……將彼此的胸膛緊貼,明明只是爲了暫時鉗制住發瘋的他。可是他身上非比尋常的熱度,溫存的氣息,令我既留戀又恐懼。
我們像是連生樹,再離開他…我就只有枯萎的下場。
雲雀…你聽聽我說話啊…
我撫上他粘著苦痛的臉。
剛才完全沒有意識的他好像回過神來清醒了點,他不再折磨我的肩膀。但最終是停不住的……如果不填些什麽在那張嘴裡,他就會反過來啃噬自己的身體。
大滴的血從手指與牙齒摩擦的縫隙中湧出, 「…不要咬手指…」 我使勁攥住他汩汩血流的指腹,心疼的蹭著他滿是血汗的額頭。
彼此緊盯對方,目光渙散遊離著,我聽到他海一般的呻吟在我耳邊呼嘯而過…
…雲雀…… 機械得啞著嗓子一遍一遍叫他…
再撐一會兒…再忍一下…
我騰出一隻手用力的抹凈臉頰上的癢,手背卻蹭到的滿滿熱淚。
我突然有種自己好像已經死去了一般的錯覺。
眼前的景象如同萬花筒折射鏡面的效果,支離破碎的鋪散在我眼前。窗外或許是夜燈散放的光暈展露出多邊形的棱角。整個夜靜得出奇。
一個小時如此的漫長…在奮力與他抗衡的拉鋸戰暫時告一段落之時,護士拿著胖墩墩的針管走了進來,眼裡擒滿是對我的憐憫與對雲雀的不滿。
「下一次注射要在三個小時之後,這已經是極限了,不可能再縮短注射間隔了,否則這藥很可能會要了病人的性命。」
再注射之後,藥效發揮的很快,他漸漸放棄了掙紮,目光也柔和了許多。
我一瞬間精疲力竭,直接癱軟橫倒在床沿。他撐著困倦的雙眼側過身無聲的將我攔在懷中。閉上眼睛好像成千上萬的星點在眼前閃爍,彼此粗重的喘息聲中夾雜著他難辨認的嗕諾。
「骸…答應我件事。」 他欲言又止,像是在觀察我的反應。
他不用說,我也明白他的想法。
「即使再有什麽問題也不可以推我進手術室…我的身體不想再被剖開任何一處…這根本毫無意義,你儘管看著我死就好…」
「等你做好心理準備…就殺了我,在我還沒有被吃的精光之前…」
我突然滿腹牢騷。
「你像是在做臨終遺囑。」
「意思也差不多…」
「巨額遺產要怎麼分?」 我苦笑。
「都是你的。」
「雲雀恭彌你面子很大,你知道我一向是最怕麻煩、卻累得一身臭汗陪著你浪費時間…我敢說自己家産肯定是你的倍數,根本不需要你所謂財團每年只夠供我一場旅行的凈利潤。所以我大可以不用在這裡費時費力的鉗制你,還要為你張羅著叫全世界最好的醫生為你診病。」
「……你回來,只是爲了叫我殺你嗎?殺了你太容易了,根本不需要我出…」
「喂……」
「我是想你。」
他難能坦然講了句實話。
字字句句糅合的聲線排列,形成了一份感情波譜。
而我只有感慨,只要面對他我就會心軟。
「或許我該用幻術讓你好過些…」
「別,」 他壓制著我的手臂, 「別在這上面浪費精力…根本就是無用功的…」
「你願意替別人活著……我卻不想做庫洛姆。」
這句話從他口中說出來,像是浸泡了多少五穀雜糧釀出的一杯酒。
我沒說什麽,淡淡的笑了幾下。 就這樣互相偎著我仿佛做了一個夢,再睜開眼睛雲雀近距離放大數倍的臉就在眼前。我的唇被什麽擦著揉著,鼻尖有不安分的東西蹭來蹭去。
感覺到腰間的手在狠狠的用力,他牽動著病床吱嘎的曖昧聲音,一寸寸的將我上衣卷起來、手難能可貴會如此輕柔。喉嚨裏哽咽的發出不易辨識的內容,像是在說「我愛你」。
我的委屈像是得到回應,被對面撲來的煽情熱流感染了莫名的悸動,我迷蒙之間伸出舌頭探進他藥苦味的口腔。
感覺得到他下身硬了不少,而我也一樣…漆黑中感覺即將理所應當發生的事情卻遲遲未來,他只是摸著我再沒有深入做什麽。
我們吻了多久,直到不真實的一夜悄然逝去。
他終於可以安心的睡著了,疲憊的蜷縮成一團緊箍著我的腰像個渴求母愛的孩子。
我卻精神百倍的思考著他剛剛講給我的每一句……徹夜不眠不休。
第二天雲雀是疼醒的,不出意料我們之間又進行了一場熱血的PK賽。
再注射止痛鎮靜藥劑之後迎來的短暫休歇,我急忙蹬上鞋洗漱了下後出去吃了點飯。
路過醫院一樓超市時我看到有賣雲雀愛吃的蟹肉餅,順便買了一堆大概會得他胃口的零食。既然像他說的坦然面對死亡,那至少要在走前一飽口福。
就這樣我晃蕩了近一個小時才回去。
然而真是沒想到上帝就喜歡開我這種無名人氏的玩笑。
我不慌不忙的推門進了病房才發現——
雲雀的床上竟然是空的。
我大腦瞬間當機,拎著沉甸甸的東西飛奔在走廊卻不知該找誰質問。
走廊拐彎處撞上同樣一臉焦急的彭格列。沒等反應過來,他一把抓住我手臂在我耳邊大喊:
「雲雀怎樣了!沒事吧!到底什麽情況!」
然後他發現了我提著東西狼狽的樣子。
「骸你怎麼提這麼多東西?雲雀人呢?剛才護士電話到我這邊說雲雀情況急劇惡化,我正好開車在往這邊來的路上……」
我顧不上再聽他說,急忙找急救室的所在位置。
手掌被盛有重物的袋子割的發紫,手裡還攥著已經被擠壓變形的熱乎乎薄餅。一切溫馨的場景像是從未發生過的,像是我無意識編織的夢魘。
軀體好像已經無法去支配一身的幻術力量,正被自己構築的假像繞的團團轉。
我像是個逃難的荒農,全無形象跌坐在手術室的門口。頭頂那盞依舊諷刺感十足的紅燈,總是在我耳邊一遍一遍的提醒著:
「我無需再進手術室,也不希望。」
「不要在我身上動刀,這樣就好。」
過了多久,再被推出來的時候,我看到震驚的一幕。
雲雀喉嚨處被捅了個直徑大約兩釐米的圓洞,從這裡插進去一只管到身體不知通往何方。連接的位置安裝一個巨大的機器,他的脖頸在這東西的對比下顯得如此不堪一擊像是不小心就會折斷。看到這一幕,一直站在旁邊的彭格列顯然是被嚇到、手不自主的拽上我的衣角。
我現在很想就這麼發動匣子將這群欠操醫生直接肢解個稀碎。
連同關鍵時刻竟然在外閒逛的自己。
他再醒來已經是第二天了。
與前幾天的光景不同,他不再亂動了——他已經虛弱到沒力氣掙紮了。
氧氣罩與各種儀器將他全部的自由沒收。身旁的心跳觀察器滴滴的響著,上面的數值可謂是有史以來的最低線。
「醫生剛才說了,咬咬牙你還可以再堅持五天時間呢。」 我對著他說,笑起來像哭。
過了好一會兒,他開始挪動臂膀摸索我的手。
然後緩緩收攏抱在掌中。
現在不是更應該是我來握你的手並安慰你的麼…
我內疚的盯住憔悴的他。
雲雀,我不願見到你被吃到肚囊空空的地步。
而被這樣對待,你也一定很痛苦吧。
撫著他蒼白的面容,心一陣陣針紮著疼痛不斷。雲雀保持著些許意識在回應我,氧氣罩下霧濛濛阻擋著視線,我卻依舊看到他蒼白嘴唇上附著著往日難得的笑。
握著的手在一點點的用力著,從緊緊貼合的肌膚那裡形成膠粘的汗液。活著的證明,生存的權利,隨處可見的現實明明是該高興的,可是爲什麽渾身都在戰栗…
心之防波堤正在提醒著,滿溢的洪水正一點點越過警戒線。
「…雲雀…」 我將不斷落著雨水的臉貼在他略有粗糙的手背上。
對不起,之前你拜託我的事情沒有做到。沒想到,一切會變成這樣…
痛嗎、悶嗎、冷嗎…需要我做什麽為你嗎。
想要告訴我什麽嗎…
被握著的手突然的用力,我急忙抬起頭。
撞上了他微瞇著的眼,瞳孔正在縫隙中移動著,然後釘在向著我的方向。
「什麽?」 我湊近他,雖然知道他無法說話卻仍然將耳朵靠過去。
收到的是拼命掙紮著的粗喘聲,不絕於耳般的撲打上心岸。
手中又是一股力量傳來。
「骸……」
我讀懂了雲雀眼中噙著的淚到底是在講給我什麽。
…原來我們一直在考慮同一個決定。
殺人無數的自己,這次卻猶豫不決。
仍舊顫動的手滑落在氧氣罩上的時候,我卻用不上力氣。雲雀眼睛儘量睜大的望著這邊,我的視線卻首先波紋滾滾。他正在用著生命最後所剩無幾的力量在乞求著我。
無法控制自己身體止不住的顫抖,我伸出的右手在半空中震蕩著,想要收回…
而他的手掌持續在用力,令我再沒有退路回頭。
窗外的雨仿佛硬是要下進我的眼裡才罷休。
每一滴嵌進我的心裡都是你,雲雀。
就在我為你流淚,我想要保護你的這一刻,我終於知道了我的脆弱。
你不在的日子我在線的這一邊輕鬆的持續著正常呼吸,完全隱瞞了想要說的話。
沿著時間軌跡如果可以追回,即使連呼吸也靜止了也無所謂。
但是誰來告訴我,在哪裡才可以找到這樣一個入口——可以有能力編織一次幻術,將你烙印在我回憶的樣子重新還原在未來將要迷失你的日子裡面。
就這樣永遠蝸居在不真實的自欺欺人之中…
只是看到你在我面前流露出的難過神情那閉上眼睛也無法消除的景象,到底會折磨我多久呢?攜帶著這樣一個累贅,要再踏過多少次輪回才可以卸下?
壓得我喘不過氣、流著眼淚,卻完全放棄不下自虐般背負著…
只要你一個笑臉就感覺不到痛了,只要你一個擁抱就體味不到辛苦了。那麼你呢?
你什麽時候才會和我相遇?
難道就不能永遠陪在你的身邊麼?
即使相伴,你也會露出隱忍的神情吧…
即使相遇,也無法認得我了吧?
根本沒得選擇的啊。
爲什麽…
我伸出手。
輕輕扯下一直以來束縛著他的氧氣罩。
雲雀,這樣你是不是就舒服一點?
「謝謝你。」
他的聲音像是從天空傳來的。
視綫的焦點濡濕了床。
淚與汗浸透了皮膚,浸透了髮絲,浸透了床單,浸透了我許久持續潮濕的眼睛。
也浸透了雲雀失去溫度的臉頰,和臉上淺水灘般憔悴的淡笑。
「…原諒我……」
他啞著嗓子,無力的吐著臨別時的囑托。
想要被原諒的人,是我才對啊……
景象靜止之時,心跳微弱持續,呼吸急促伴隨。
我終於還是伏在尚未冷卻的胸膛上毫無遮掩的放聲大哭起來,心裡不斷發出震耳欲聾的崩塌聲,剝離了多少我佯裝堅強而構築的防禦。
雲雀憐愛般的柔順我腦後的長髮,一點點的傳遞至我心是溫暖。
直到多久過後,那隻手掌輕輕的停在了某一點。
五個冰涼觸點緊貼在髮絲上溫柔的攢住。
這樣持續了多久…
再也沒有滑動的軌跡。
「…嗚…」 有什麽堵塞住聲道。
我的淚最後一次傾瀉而盡。
記憶迅速倒回還健康的他,有些虛幻的細緻的珍惜的吻我、抱我。
不論未來可能會記得或遺忘,那些殘留在我身上體內每個角落的,他的觸感。
再體味時,將永遠都是一片暖。
「生日快樂。」
下篇 遍佈蟲蛆的土
最終我們終於為雲雀尋到一處安靜的位置,並且距離並盛很近。
在這個常有日照山坡上,我們找到陰宅的主人,好說歹說請他為我們再讓出一塊地方。緊接著幾天,按照日本的習俗一絲不茍的將他下葬了。
之後幾天我本是爲自己放假的,結果下葬當晚手機傳來義大利總部那邊緊急召喚的訊息。據說襲擊雲雀的家族以此為導火索企圖掀起正面衝突,我們被殺了個措手不及正位於劣勢。只好匆忙整理好行李,趕在第二天早晨那班飛機前見一眼雲雀再走。
第二天的並盛,下起了細密的雪。
我和草壁等隨從帶著一束花來拜祭,他們站在我的身後,可以間隙聽到幾聲嗚咽。
並不寒冷的風徐徐吹過時,我捕捉到一絲常在雲雀身上可以嗅得到的氣息。
原來這裡一直是屬於你的。
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為何存在於這裏,爲什麽要註定經歷六世輪回。自己從這些漫長的歲月裏學會的只有患得患失、無情冷漠,而後無緣故的成了一名殺手。或者我根本不需要表面上的溫暖與歸屬,所謂的家只不過是遮風擋雨的場所。然而當多少個四月飛速逝去,我在沒有終點的環形路上盲目的繞啊繞,終於發現自己其實什麽都不是。
可是會有人在長途電話裏只爲聽你一把滿是厭煩的聲音就可以滿足的掛掉電話麼?會有人只在酒醉之後才會笨拙的講給你樸素的情話麼?會有人在你落淚的時候什麽都不說只是握住你的手目不轉睛的望著你麼?會有這樣一個人麼?
我轉身離開。
突然,一陣逆風襲來,捲起我風衣長擺和四周細碎的沙土。
那束鳳仙在我身後簌簌作響,撩起的花瓣劃過我的臉頰,粘上我的頭髮,墜在我的肩膀。像是一場陣雨,追趕著躍過我,將全部的香氣連同生命紛紛飄舞、隕落在我面前。
低下頭,視線裏有一瓣靜靜的躺在腳邊。
我滿是淚漬的臉終於懂得要笑著說。
「要跟著我走嗎。」
全文完
注:鳳仙的花語是「活在回憶裏」
PR
對這篇文,我有話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