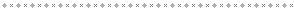
[PR]上記の広告は3ヶ月以上新規記事投稿のないブログに表示されています。新しい記事を書く事で広告が消えます。
『 雨売りの私のせいだ、土砂降りに傘を広げた。』
不經意而持續的循環運動沉澱地久了,就更名為習慣。
「請慢走。」 山本武收拾杯碟抹凈餐桌,抬頭瞥了一眼日曆。
雲雀來店裡的時間總是有些晚,故意等店裡客人散去大部份之後、臨近打烊前一兩個小時。坐在一如既往的角落里,一個人靜靜呆到三兩客人結帳離開、小武把空凳子整齊地摞在桌上、掃帚划動地板的刷刷聲也停下來、山本父親一聲悠長的哈欠。
然後一隻手輕輕地推醒還在混沌中掙扎的自己。雲雀撕開粘緊的眼皮,發現山本武正蹲在桌邊。他下巴抵著在桌面,輕聲對自己說,
「已經十一點了,雲雀。」
「…唔。」
可其實雲雀還睡得正懵。支著牆壁才勉強站直了身體,抓起書包掏了一陣才拿出幾張紙幣擱在桌上。稍微可以清醒一點了,隨手扯扯衣角理理劉海,邁著左腳絆右腳的步調踏出店門。
有一次山本武跟了上去。
雲雀厭惡地瞪了山本一眼,他便退後拉開了兩人的距離。如此反復直到雲雀默許地無視了山本武的尾隨,一前一後相隔了十幾米遠。小武眼裡噙著前方細瘦的身影在夜風中搖擺不定,或許膚色太過蒼白、那道曾見過的傷痕時隔一個月依舊攀在他的頸子上,這種距離也看得清清楚楚。
順著壽司店前的街往東邊走、會穿過一條鐵路,就進入了并盛町中心區。對立的兩個世界,背後還是靜謐的夜、面前的霓虹正曖昧地魅惑男男女女。
又跨過幾個十字路口,雲雀忽地停下了。沒有拐進右側虛掩的店門,也沒有回頭給山本任何信號。像一尊雕塑,維持著注視前方的姿態,行人們擦身而過時淹沒在其中的細瘦身影看似不堪一擊。
山本顧不得間距這回事,在人流中穿梭前行奔到雲雀身邊。
他黑曜的眼瞳毫無情緒,小武順著那道視線凝望的方向看去——或許是那輛車。約四五十歲的一對情人、亦或者是夫婦,他們在車旁接吻道別。男人衣著裝扮可以推斷出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女人雖中年卻風韻猶存。兩個人互說幾聲耳邊話之後,女人轉身走進一間酒吧、男人依依不捨地揮別、最後鑽進轎車。
車駛遠了消失在車水馬龍中,小武扭頭問雲雀。
「認識的人?」
「恩。」 雲雀從兜裡掏了一根煙出來。
山本武會衡量兩個人的距離,清楚言多必失的道理,懂得該如何對待你。可他記憶猶新還能想起方才的場景,那時候你佇立在人群中,
——背影滿溢悲傷。
「熟人?」
「恩。」
他想講話,他要說什麼,你會回答嗎。
「親人?」
呼出白色的煙在空中突然尋不到蹤跡。雲雀冷冷地瞥了一眼山本武、眼眸刷上灰暗卻複雜的色澤,低沉地說:
「戀人。」
山本武一個人站在熙攘的街、目送雲雀頭也不回的走進酒吧,很久之後撿起了他丟在地上還燃著火光的半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
「阿武——」
老爸的聲音打斷了小武的走神,他急忙把手裡已經反復擦拭了幾遍的碗碟碼進櫃櫥,轉身進了廚房, 「什麽事?」
山本父親擠出不自然的笑容,「把這個拿到三號桌。」 豆大的汗從額頭滾下來,嘴唇失了一層血色。
「老爸,」 他伸出來想要探父親的額頭,「你臉色怎麼…」
父親拒絕了兒子的擔憂、推開他的手, 「出了太多汗有點低血糖吧,沒事的,」 說著去拿擱在一旁的漏勺,手卻在勺柄邊上抓了個空。整個過程山本武看在眼裡。他改用嚴肅認真的口吻,不像建議更像命令地講,「上樓休息一下,老爸。」
「還是到打烊再說吧。」
「店裡只有我一個人也可以。」
「你不行的,兒子。」
他沒想到父親會這麼說,突然接不下去了。
兒子的一個頓號令山本剛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急忙擺手說阿武我的意思是說你還——
「沒事,」 他攔住父親的解釋,「客人該等急了,我去上菜。」
竹壽司店門前的街漸漸被愈濃的路燈照得靜了。腳下踩著的石土發出吱嘎聲,雲雀停在店門口看了下手錶。還有半個小時打烊,他想時間還算夠用。
手還沒來得及伸出來,門卻自己刷地拉開了。
迎面撞上滿頭大汗的山本武。
「啊、雲雀,」
山本小心翼翼地弓著背從店裏面走出來,雲雀注意到他身後背著的人。 「抱歉,我們今天提前打烊了。」
雲雀搖頭, 「怎麼了。」
「沒事,老爸不舒服、我帶他去醫院看看。」
一直耷拉在山本肩膀的腦袋動了動,吐出一聲虛弱。 「…哦…是雲雀啊、」
「您好,伯父。」 他打了聲招呼,又問山本,「怎麼去。」
「運貨的車停在車庫那邊了,」 山本一手拖住背上不斷往下滑的父親,一手鎖上店門, 「這邊晚上就沒什麼車經過,我打算背老爸直接去那邊的主幹道打車。」
雲雀點點頭沒再說話。兩個人視線交接維持不到兩秒鐘,小武就轉身快速往路一頭走去。
他不想讓雲雀看到自己這個樣子。這之前,發現癱坐在廚房地上的父親已經意識不清時,他還恐慌地不知所措。結果推開店門,這個人就站在門口,自己臉上來不及遮蓋的狼狽與幼稚,全部一覽無餘。
小武走了一段距離之後才回身望了一眼,雲雀原本站著的地方已然空無一人。他低下頭苦笑了兩聲。然後加快了腳步,一面慶倖著、一面失落著,走完了剩下的路。
這一夜比他想像中要沉重得多。
領到檢查結果,小武把核磁共振的黑白膠片送到急診中心,繃緊了神經盯住查看膠片的醫生。
醫生斜眼打量山本武幾下,才遲遲開口說, 「叫你家親屬來吧。」
「我是他的兒子。」 山本有些怒氣,生硬地強調了一邊。
「未成年吧。」
「…是。」
醫生把膠片擱在山本武面前,「你父親沒什麼事,不過要做個手術。」
「吶,做手術要家屬和院方簽署合同,」 醫生歪坐在凳子上,手裡把玩一根筆, 「未成年人是不具備簽署資格的,懂嗎。」
「我不管你什麽逞強心理、不過別拿你父親的生命開玩笑哦,小子。」
小武頓時無言以對。沉默片刻他裝好檢查結果單,站起來鞠躬后便默默走了。等到把全部費用結清之後,醫生才准許急診室放人。山本父親被推往病房的路上,模樣頗像護士長的女人攔住山本武。
「等一下,給我看看住院手續。」
「急救中心那邊的醫生說可以先入住再辦。」
「那邊的醫生?」 眼鏡片下的眼神銳利地掃視山本武, 「住院部有住院部的規矩,哪邊的醫生到這兒說話都不算數。」
推車的護士猶豫不決地舉著吊瓶望向對峙的兩個人、車就停在病房門口要進不進的狀態,小武只好雙手合十畢恭畢敬地請求說,我這就去辦、求您先讓我父親進去。
護士長皺眉,「現在床位緊缺著呢。」 說完勉為其難地輕點下頭。 護士們拿到了准許令,便推山本父親進到病房安置。小武連忙再幾個九十度鞠躬感謝。
穿過人群跑下樓的腳步卻踩不穩、山本武險些從樓梯上栽下去。腳下的速度越放越緩,在距離支付窗口不到兩米的時候,他終於停了下來。
排隊的隊尾就在眼前、小武掏出手機。
—— 姑姑,是我。
山本武記不得自己第二天是怎麼回的家。向學校請了假,老師關切地約好了放課後的家訪時間。一路在公車上昏昏沉沉的,眼睛放空狀態瞧著窗外的景色,腦子里根本是糨糊一團但在努力做著規劃:要先整理好父親的衣物和其他用品、再去醫院旁的超市買些吃喝用的、晚上就在醫院過夜轉天直接去學校。
只是計劃趕不上變化。 回到家后,他小心翼翼推開父親房間的門。走進這間有些陌生的臥室,他站在房間的中央環顧四周零零散散的桌柜箱包、拉開抽屜櫃門隨手翻了翻,終於拄著頭苦苦地笑起來。
他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做。
該拿些什麽、用什麽裝、老爸他需要什麽、這些東西在哪裡。對這個家這棟樓只有自己的臥室他足夠瞭解。所有的物品井井有條收納在各處,從擺設到工具,他明明每一件都熟悉到甚至叫得上名字、聞得出自己的氣息,也生疏到仿佛走進陌生人的家。
山本武在家整理了一天的東西。把晚飯打好便當一起送到醫院、和姑姑聊了幾句父親的情況后就被姑父好說歹說勸回家休息,小武到家時天已經暗了。
他寧願留在醫院照顧父親。捲起店鋪門口的防盜鐵皮簾,營業招牌卻沒有擺出去。山本武坐在空無一人的店鋪里發著呆,面前是攤開的空白作業時不時地分心寫上幾筆。路過的熟客們陸續推門進來詢問小武父親的情況,他疲憊地笑著安慰說,已經沒事了、請放心吧。盡全力地沒讓人聽出句尾的哽咽。
天空顏色加深了幾層,陸陸續續屋外的夜攤熱鬧起來。和店裡的冷清對比太過強烈,小武拉開店門默默地放下鐵簾、像是緩緩阻隔開兩個世界。
這時,淹沒在喧囂中的腳步聲戛然而止在身後。
——已經打烊了么。
他是多麼難得才從接收到糾結成一團的聲線中找出這根。
這麼說或許有些矯情。但小武還拽著滾軸線的手幾乎沒得力氣再握下去,講話的主人還是那樣稀鬆平常慢條斯理,可這把聲音硬生生扯住了他想偷偷咽下的一口痛。
你是不是來救我的那個人?
「沒關係,」 山本武把捲簾放到底,然後扭頭對雲雀說, 「從後門進來吧。」
通向二樓的後門,那段走廊陡峭又漫長。交疊錯亂的腳步聲,在黑暗中重重迴響。
「等一下,」 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只聽得到鑰匙串抖動撞得叮噹亂響,以及雲雀在呼吸時習慣夾帶的一點鼻音。
如同一場噩夢席捲之後風平浪靜,明明應當感慨頗多彼此卻只剩無言。
只是,一旦開口的話,需要解釋的東西實在太多。
兩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店裡,廚房烏冬面的香氣溢滿周身。雲雀掏了掏褲兜,翻到根煙點著。小武望著雲雀嘴里的煙,一明一滅間堆積出一層煙蒂。
「是什麽感覺?」
「嗯?」
「這個。」 山本武指了指雲雀叼在嘴裡的煙。
雲雀遞給小武, 「試試麼。」
對方正要接過來,他又忽地想起什麽收回去。
「忘記了,你不能抽。」
山本武笑著奪過雲雀的煙吸了一口, 「我已經不打棒球了。」
雲雀拄著頭,等山本武把話講完。
「還在打球的時候總考慮一旦失去它了自己絕對會死掉吧——」 吸出的氣體從嘴裡出發僅僅經過喉嚨打了一個迴旋便從入口處離開了。
還真是天然的煙盲,雲雀心裡想。
「結果上了高中選了一所體育社團很差的學校,我也沒報名社團,恍然間一年半我都沒再摸過球棒。」 他無聲色的笑, 「原來放棄一件東西,只靠時間就够了。」
「不過話說回來,不該抽煙的人應該是雲雀吧。」
雲雀用同樣招數奪走了小武指間的煙, 「我就是風紀的規則。」
山本的腦海裡閃過那件普通的米色校服,「那…」
「吱——」
廚房的高壓鍋鳴叫截斷了他的好奇。那些被吞沒的話,餘音繞梁在他唇齒間漸漸地化開了。
山本父親珍藏的那瓶清酒,就這樣被兩個人喝得精光。
小武撐著額頭,眼前的景色像是許多張幻燈片頗不連貫地摞疊在一起播放。牆上的鐘,時針剛好和分針併攏指向最上方。
「今晚在這裡住吧?」
沒回應。
他看著雲雀已經爛成一灘泥斜歪在桌上打盹,心說這個人是沒什麼酒量的吧。一直以來只見過他喝日本酒,度數本來很低可幾杯下肚就會醉。方才的酒喝到一半時雲雀就已經撐不住了,結果山本武不僅吃了面還喝掉了幾乎剩下的整整半瓶。
「雲雀、醒醒、」 他走過去攬起雲雀, 「要睡去樓上睡。」
雲雀喃喃幾聲聽不清在嘟囔什麽,不過雙腿還是配合支撐著站起來了。小武拉住雲雀把他手臂架在肩上,握緊的那雙手蒼白冰冷,一用力按就會在皮下滲出斑駁的充血印記。好不容易到了臥室,把雲雀安置在床上、正要去掉他腳上的鞋,他卻緩緩地坐了起來。
「我自己來…」 雲雀伸出手去解鞋帶。
小武讓開、背抵著床邊坐在地上, 「要喝水麼。」
「唔,」 接過玻璃杯、他解開了兩個襯衣扣子透氣,小武眼神順著他吞咽而上下滑動的喉結下移、釘在粉白肌膚包裹的凸出的鎖骨上。
眼神或許是藏有溫度或聲音的,我在望著一個人的時候,那個人如同接收到信號一般也撩起眼簾。無可避免地四目對視雖狗血卻總萬能。
「怎麼了。」 雲雀把喝空的杯子遞給山本。
山本瞧了一眼雲雀,又收回視線。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或許你的這份愛只是個錯覺。」
雲雀愣住片刻,緊接著挑起眉語帶戾氣,「不懂你的意思。」
小武能夠感受到那雙凜冽目光,卻沒打算正面抗衡,只是懶懶地靠著床沿看天花板的燈。
「我啊,曾經有段日子也非常喜歡我的數學老師。一次機會我和她告白了,沒想到她回答說願意等我國中畢業。」 說著他淺笑, 「拼了命考上了高中,我拿著入學通知書到她家樓下,開門的人是她的丈夫。男人問我是誰,她站在他的身後只看得到眼睛依舊那麼漂亮。」
「那雙眼睛眨了眨,然後說,我不認識他。」
話音落下,只是一刻的沉默之後,雲雀啞著嗓子說,所以呢。
「我意識到、錯不在她。我只是把對母親的尋求,過度加注在別人身上,就錯以為那是戀愛。」
「呵、」 雲雀一聲冷笑, 「山本武。」
小武回過頭看向床上的人, 「雲雀,其實你對——」
「你瞭解什麽,」 雲雀不客氣地掐斷他的話, 「有資格評論我的事麼。」
「我是不瞭解,只是覺得雲雀不該是這個樣子的,」 山本無視雲雀眼神散放的慍火,放緩語調講, 「雲雀一直很冷靜很聰明,明白我的意思,不是麼。」
「明白。」 雲雀踩上鞋子抓起衣服和書包, 「我非常明白,」
說罷毫無徵兆一腳踢向小武的肚子。他來不及應付這一腳,結結實實的挨上了。一聲鈍響之後,他頓時痛到弓起身體止不住的乾嘔。
「可悲的戀愛,被耍了呢。」 雲雀盯著蜷縮成一團的人,「看不慣別人比你好吧,嫉妒吧。」
小武發不出聲音、只好吃力地撐起身體。
雲雀鼻腔哼出一聲輕蔑,轉身走開。
眼看著打算開門的雲雀就要觸到門把手,他鼓足了勁扶住櫃子站起來。衣櫃被推搡的晃動了幾下掉落些灰塵灑在他的頭頂和肩上、跌跌撞撞間雙腳扯倒了多少東西發出災難性的碎裂聲、他一手捂住肚子一手盡可能去拉住眼裡唯一的救命稻草。
「雲、」 他死死拽住那條書包帶絕不放開, 「…雲雀、」
門被開了一道縫,雲雀扭頭充滿殺氣的目光刺過來, 「放手。」
小武搖頭,捂著肚子的手伸過去用力推上門、上鎖。
「你想死是吧。」
「你說的對…」 他抵在門上,臉上滑下滾滾汗珠滴進柔軟的地毯。
雲雀冷笑, 「那我就成…喂、…」
小武沒時間聽雲雀講完,更不能給雲雀機會出手。
搜刮腦里所有記得住的情感戲,學著遊刃有餘的男人們的招數,他硬著頭皮拖住雲雀的肩膀,一把拉近自己。雙手捧住因酒醉熾熱而殷紅的臉龐。
突發而至這一遭襲來,雲雀深黑的眼眸縮小了幾圈、怔怔地望著山本武。
「你、你說得對、」
他此生都沒有做過這種嘗試。
當兩張臉距離這麼近的時候該如何做才能順理成章。時間不可能受人類控制隨意慢速播放,只是不足一兩秒的時間內他們有一次對視的機會,叫你讀懂他眼裡滲出的話。再晚一秒鐘、或許你不會再給他機會反而會要了他的命。
「我很嫉妒她。」
隨即對準微張著像似要講什麽的嘴唇笨拙地咬下去。
牙齒反復的撞在一起。兩個人心知肚明彼此都是毫無經驗,又不想尷尬的結束,只好蠻橫地持續下去這個兇殘的吻。
雲雀緊張到戰慄,瑟瑟發抖之間攀住了小武的衣袖,身體卻還是不忘記要逃。小武翻轉過來把他死死抵在房門上不讓出後路,結果是許久過後兩個人吻到腫脹的唇才稍微鬆開。
令人難忘的第一次舌吻。
他貼著雲雀高溫的額頭,鼻尖相碰同時四目對視。
「…覺得噁心麼,」
「我要吐了、」
「因為我,還是酒?」
他在選擇項中間只猶豫了一秒,卻被對方發現了。
沒等雲雀回答,小武就侵上他漲紅的耳垂含在嘴裡用力地吮吸。舌尖繞著雲雀耳廓打圈,惹得懷裡的人氣息亂成一團。身體一陣陣震顫,惹得人禁不住想要疼愛他。
「原來…雲雀你並不討厭,」
「我沒那麼說!…唔…」
雲雀抗拒地將手臂橫在兩人之間,小武抵死不願放開纏在他腰間的手。就這樣糾纏著,混亂之中山本武解開了雲雀的腰帶。
被酒精和情熱沖昏了頭腦的人立刻反應過來、不停地掙扎起來,「喂…、」
「不、不…我只是、」 小武想不到用什麽可以替代那些羞於張口的詞彙,手蹭著雲雀光潔的小腹滑進內褲里直接觸到已經微抬頭的物體,不等雲雀意識到時、頗虔誠地握住了它。
「!」 雲雀顯然受到驚嚇,可要害被牽扯著限制了他抵抗的力度。 「放開我!」 汗水鑽出細密的髮梢,山本武看得出他的確在品嘗前所未有的焦慮。他只好想辦法速戰速決。
一手扯下自己的褲子,露出早已腫脹的男根,雙手將兩個人的分身握在一起。不願低頭看的雲雀將重重的頭搭在山本武的肩膀上,幾分虛弱的說,「…你瘋了嗎、」
小武蒼白地笑,接著沿雲雀的脖頸線條吻上肩膀、鎖骨,「都是雲雀的錯啊…。」 說完,遲疑的雙手動了起來。
「…山本武…啊…唔…」
一旦開口,情不自禁的哼吟也會洩露出口。
「…舒服嗎、這樣…」
「……不、啊、」
雲雀想抿住嘴唇,可不想被對方看到自己隱忍的狼狽。他抓不清眼前的景象,想叫誰的名字不知出於什麽目的。下身被略粗糙的手掌和另外一根羞恥物摩擦帶動著,一陣陣快感與無助令他哭笑不得。不甘心、想否認,可雲雀此時簡直是不知道除了死死攀住眼前這個男人以外自己這副顯然沉淪了的身體還能放在何處。
「…雲雀,雲…雲雀…」
爽朗的聲音如今低沉地叫著自己的名字。
「快、快射吧……」 話沒說完,雲雀空蕩蕩的眼前像是閃過一道光。巨大的脫力感接踵而至,他鬆開環著山本的手臂往下滑。卻被對方穩穩托起。
「…啊、射了嗎雲雀…好可愛…」
「才、才沒…」 雲雀羞恥地把臉埋在手臂里,「…混蛋、這算什麽……」
「…好啦、好啦…」 小武笑著扯開雲雀的遮掩,側頭吻緊他的嘴唇。
再醒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兩個人衣衫不整地擠在同一張床上。他翻了個身側躺,地上還躺著昨夜糾纏后弄倒的茶杯茶壺、碎的碎裂的裂、連同翻了個的矮桌,可憐地攤在地毯上。腦袋裡的記憶也是細碎成一堆,他撿起一小塊,裏面是雲雀在自己手中高潮時迷蒙的眼睛……下身迅速激來一股電流令他立刻打住了念頭。
小心翼翼地起身打開衣櫃掏出被子給蜷縮成團的雲雀蓋上,簡單收拾了地上的殘局。再瞧背對自己還睡著的雲雀,他換了身衣服便出門了。
肚子還在痛,去探望父親之後小武順路買了膏藥貼,又去家附近的市場晃悠了半天、買了些蔬果蛋肉才繞回家。天陰沉著臉,他拎著購物袋抬頭仰望幾隻燕子嬉戲低空飛過頭頂。
然後他就看到了雲雀。
他站在自己家的二樓陽臺、把地毯搭在晾衣杆上拍掉殘留在毛絨里的碎渣,或許沒有意識到有人在注視他。
山本武看得出神,兩隻腳漸漸忘記了要走。
有人說,當你想和一個人一起旅行,你只想旅程儘快開始。
當你決定和一個人一起共度餘生,那麼從這一刻起,生命重新開始了。
小武愣在路邊幾秒,才邁開了步子。那腳步越來越快、越來越快、直至他不顧一切地飛奔起來。風呼嘯在耳邊叫囂著嘲笑著,腹部傳來明晰的痛,宿醉使得眼前混沌不清,手裡的東西纏得手掌一道深深的血痕。家門沒鎖,他一股腦把東西丟在玄關,來不及脫掉鞋子,踩踏地板的咚咚聲響與他的心跳共振,他瘋也似的闖進了臥室。
正巧雲雀也剛從陽臺鑽進屋。看到進來的人氣喘吁吁一頭大汗,雲雀問,「怎麼了。」
他哽住,才說,「我以為你走了。」
你不知道他抹掉了這句話裡多少委屈與欣喜。他想握的不是細瘦的手腕、而是冰冷卻柔軟的手,發誓會好好的握住不會再放開了。他這麼想著,沒有這麼做。那時,掌心包裹的手滲出一片不健康的血色,他擔心一旦握住了便松不開,要你的手在自己的掌心裡止不住地淌血也不要讓步。
雲雀指著寫字桌上的一串鑰匙。
「我走了,你怎麼進來。」
他以為門是自己忘了鎖。
「…昨晚的事、…對不起。」
「只是喝醉了而已,」 雲雀勾起淡淡一抹笑,口氣清淺的如同窗外浮起的雲, 「又不是女人,沒什麼大不了。」
他想握的是冰冷卻柔軟的手。
他這麼想著,沒有這麼做。
小武鬆開暗暗攥緊的手掌,抹掉了鬢角滑下的汗。胸腔躍動的心臟漸漸停了下來。
他拉開臥室的門,笑著回頭問,「餓了吧,給你做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