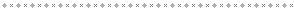
[PR]上記の広告は3ヶ月以上新規記事投稿のないブログに表示されています。新しい記事を書く事で広告が消えます。
『何もかもを閉じ込めた瓶の中、ただ僕は愛しさを押し殺した。』
小武推門進來時病床空著,年輕護士在更換床單和被罩。
「又來送飯了嗎,真孝順呢。」 她眯著眼睛笑, 「你父親被安排去做定期檢查了。」
他點點頭,「我在這裡等。」 轉身將昨日殘留的保暖飯盒整理好,他注意到姑姑擱在床頭的提包裡有一封信,上標有「病歷本」的手寫字樣。
好奇心的驅使令他難以克制探知的欲求,終於還是躊躇地抽出來信裡的東西。
有本病歷和幾張收據,以及一張對折的十六開紙。他展開來看——
一式三份的手術協議書,甲方落款處是父親的字跡。
在『除醫生失誤操作以外,開顱手術若導致患者腦部受損、院方不負主要責任』后跟著姑父的簽名。
「腦膜瘤,腦垂體鈣化…。」
山本武不由地念出了聲。 換好床單的護士將被褥鋪平,應和道,「很辛苦呢,不到五十歲就要遭罪。我老家的母親也是,手術之後留了後遺癥…唉。」
「會有什麽後遺癥?」 小武問護士。
「樂觀一點就是癲癇啊失語啊、嚴重的話就是偏癱、精神障礙甚至長期昏迷吧。」 護士抱起替換下來的床單, 「問題是這些癥狀也會幷發,我母親就是偏癱伴有失語。」
「祈禱你父親能夠順利奪過難關,」 她歎了口氣,推門離開。
坐在父親的翅膀下,不知道他淋了雨。
山本武閉上眼睛。
落日將身體拉伸成細長黑線投射在地面,從醫院回來的這條路上,行人們紛紛踐踏自己的影子。
走著走著,他驀地決心掉轉了方向。
放學時間,校門口人潮湧動。
倚著校門外的一棵櫻樹,斜肩背包身著淺灰西裝制服的山本武在人群中格外凸顯。擦身而過的女生們嘰嘰喳喳或竊竊私語、討論著他一身筆直一臉英俊,期待又故作膽怯地、希望能被注意到。
然而他只是專注于掃視、尋找著。直至人群散去的差不多、只剩還在進行社團活動或是放課補習的學生停留在校內,守門人慢吞吞地推上大門鎖好、只留了條狹窄通道。他擔心自己或許漏掉了那個人,亦或者對方已發覺自己卻蓄意避開——
雲雀已近半個月沒再來過店裡。
再等了多久,天暗了下來。
亮著燈的教室越來越少、操場上的人影也逐漸不見。
小武焦慮地詢問守衛人員,「可以讓我進去嗎?」
「對不起,沒有身著并盛高中的校服,是不允許進校園的。」
「哦…謝謝。」
他只好決定離開。剛抬腳走了幾步,身後傳來了一把熟悉的交談聲。扭頭看,果然是草壁哲矢,只是同行的人並非雲雀。
他佯裝巧合相遇、走上前說, 「呦、草壁先生。」
叼著煙頭的男人先是側目瞄了眼、隨即驚詫地說,「是山本君嗎?」
「真是好久不見了!現在在哪裡,過得好嗎。」
「在鈴蘭高校,老樣子。」
「哦、離這邊挺遠的嘛,」 草壁將煙踩滅, 「今天來這裡見同學老師的?」
「不…」 他猶豫片刻, 「草壁先生、現在和雲雀還有聯絡嗎。」
草壁失笑、搭上旁人的肩膀說, 「那是當然了,我們永遠都會跟隨他的,忠心不二。」
「那麼,想麻煩草壁先生你、能否告訴我雲雀現在在哪。」
「這…我還真不知道。」
「欸哲矢大哥、」 在旁的男人突然插話, 「雲雀大人是去教訓上竹那群傢伙了吧,還叫不許我們插手,你不記得了么,他還——」
「咳咳、…」 草壁打斷了他,男人立刻意識到自己多嘴了,「啊抱歉抱歉…」
氣氛略顯尷尬。
頃刻沉默后,小武向后退了一步、緊接著彎下腰深鞠躬。
「喂山本、你…」
「拜託您了、請務必告訴我,這對我非常重要。」
短暫無言過後,草壁終於歎了口氣。
他指著落日的方向, 「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到河邊,然後向東不遠處的廢棄工廠,他在那裡。」
小武抬起頭、拗出一對笑渦。道了謝後正要轉身離開。
「喂、山本,」 草壁攔住他、暗地將一把蝴蝶刀順進他的衣兜裡, 「注意安全。」
山本武在工廠後身的小塊空地上找到了雲雀。
他的淺杏色校服蹭有斑斑駁駁的污跡,像是剛經歷過混戰。地上躺著幾具哀嚎的軀體,雲雀單腳踩在其中一個男人的胸脯上、冰冷的拐抵著男人的眼窩,他的嘴唇動了動、便不留餘力猛力扎下去——
只聽淒慘的嘶吼驚起了附近一群鳥兒,回音環繞樓間漸漸消散開來。
在旁目睹此景的一位金髮男子,頗有頭目的氣質。他邊鼓掌邊走近雲雀,身後跟進五六個黑衣打手,手裡拎著鐵質的球棒。小武輕手輕腳繞到雲雀身後的一堆垃圾後面,靜觀其變尋找著時機。
「委員長的氣勢依舊不減當年呢,」 金髮男巧笑, 「拜您所賜、我在監獄里蹲了四年,這才放出來沒幾天,就聽說您已經轉行不混風紀混黑道了?」
「有屁快放。」
「據說上竹區現在也是您的地盤,還請您把它的管轄權物歸原主。」
「真不巧。我原本有這個意思、不過現在我改主意了,」 雲雀收起拐,做好再出手的準備, 「要怪就怪你那弟弟。」
「您頸後的淤痕是我弟傷的沒錯。不過啊,您可是直接廢了他一隻右手哦。」
「所以呢。」
金髮男掏了掏耳朵, 「今天我也得廢了您的右手,作為附加補償。」
雲雀啞然失笑。
「好啊。如果你做得到,這隻手就送你。」
頃刻間,雙方幾乎同時出招。
尾隨的幾個打手將雲雀包圍在圈裡,在他專注與金髮男人交手的同時、打算從背後進攻以牽扯他的精力。小武從口袋裡掏出蝴蝶刀、趁這群人伺機下手之際一躍而起。
若比心狠手辣,山本武截止現在所殺之人坐得滿一間教室。
早先他還記得死在自己刀下時的抽搐身軀和扭曲表情甚至名字,再過不了多久記憶力如同吸附過多水的海綿,用力擰之後幾乎榨幹了全部。
他反握住蝴蝶刀,扣住黑衣人的雙臂、對準脖頸的動脈位置適度地劃了下去。
金髮男子訕笑, 「委員長原來叫了幫手來嗎,這可不行哦——」
話音未落就重重承受來自對方的猛烈攻擊,球棒與鐵拐霎時摩擦迸裂出火花。雲雀愈發施力、雙方抗衡的僵持局面開始發生偏轉,金髮男逐漸被逼往弱勢。
「沒有幫手,照樣收拾得了你。」
雲雀醞釀出全力以置之於死地、卻不料余光的視野里察覺有黑影蠢蠢欲動、企圖從身後夾擊自己。瞄準金髮男人腹部屈膝一頂——對方哀嚎著跪倒在地,手中的力氣散去了不少。俄而,剛空閒出來的冷拐又得招架在後身黑衣打手已劈下的球棒,頃刻間金屬的碰撞不堪入耳。
在與黑衣人糾纏之時,金髮男人從地上踉蹌地爬起來、蹭掉嘴角的血,
「我說、委員長啊,」
說著從腰腹側摸索出把手槍。槍口還栓有消音器。
「到底是誰收拾誰…」 上膛、對準前方, 「還講不好呢!」
奸笑聲並行,「去死吧——」
雲雀撂倒了黑衣人,卻連回身都已然來不及。
這一槍或許躲不掉了,他想。
金髮男人扣動了扳機。
幾近同時,身體竟被人從後方捆緊。他聽到子彈穿透肌肉時發出捏碎番茄般的悶爆聲。
有誰的嘴唇貼在自己的耳側痛苦地低吼,滑落。
來不及做更多思考,雲雀奪過山本武手中的蝴蝶刀,轉身投射出去——
目標命中金髮男握搶的右腕。
男人連連叫疼、槍抓不住掉在地上。他迅速奔過去掠走槍,順勢將金髮男人踹翻在地。
「你的這隻手,我要了。」
語畢,一腳踩上還扎在男人腕上的刀把,硬生生穿透了他的手腕、被釘在地上。
震耳欲聾的悲鳴,響徹了整個黃昏。
「雲、雲雀、你、有沒有受傷…」
寬大手掌堵住傷口,汩汩血從手指的縫隙中滲出。
「沒有,」 能聽到繁碎的踩踏聲向這邊趨近。雲雀遲疑一瞬,將校服脫下、裹在山本武的傷口處以掩人耳目,拉著他鑽進兩棟廠房之間的細窄夾縫。
「我們走。」
四周場景被飛速拋在腦後,仿佛道路兩旁築起模糊的墻。
緊追著的腳步聲叫駡聲漸行漸遠,山本渾渾噩噩間像是做了一場焦灼的夢、可腳下還在機械地被那個人牽扯著向前運動。除了雲雀被風吹起的黑髮掃過自己的臉頰,其他一概捕捉不到知覺。
跑了多遠,幾乎僵硬的軀體忽地不受控制、栽歪了一下便再也支不起來了——
小武來不及叫前面人的名字,恍惚之間竟已經歪躺在冰冷的石板路上了。
可他還沒失去意識。
感覺到被拖拖拽拽扯進了一個濕冷的空間,沼氣瀰漫中混有發黴的腐臭。他仰起頭依靠冰涼的牆壁癱坐著,深深汲取氧氣攢足了講話的體力。
「雲雀…那群人、」
「閉上你的嘴。」 話語中聽得出幾分怒氣幾分嚴肅。
蹲下身扳開了山本捂著傷的手、他仔細查看著。
子彈好像沒有留在裏面。 舒了一口氣。
一張泛著蒼白色的嘴虛弱地叫,「雲、雀…」
「你很吵。」 將校服的裡襯扯下來撕成一條條、再一層層緊纏在傷口處,「忍著點。」
雲雀抹掉順著鬢角滴落的汗時,沾在手上的血不小心蹭到臉頰。
小武吃力地伸手夠過去, 「…唔、…」 用食指拭去了那道血痕。
他沒有拒絕這份觸碰。
那根手指卻開始得寸進尺地四處徘徊,有意無意掃著自己的嘴角、臉頰——
殘忍又卑鄙的一種試探。
待到傷口暫時被強制止住血,雲雀才抬起頭冷冷瞧山本武。
「玩够了沒有。」
白紙般的一張臉、畫上生硬的笑臉,少年憔悴地點頭。
人類,
「手臂、沒知覺了呢…」
「會恢復的。」
是由矛盾構成的。
「呵…這麼一來,想打球都沒可…能了。」
「再等等,草壁馬上就到。」
寂寞,
「…就這麼逃走了,雲雀一定…很不甘心吧。」
「逃走?」 他睥睨,「注意你的措辭。」
不寂寞。
「很想殺了,礙、礙手礙腳的我吧…」
「哇哦,你挺清楚的嘛。」
戀慕,
「…可是終於能…見到你、了、…」
他像是困極了,講著講著禁不住睡過去的模樣,看起來是泰然的、柔和的。
雲雀叫了山本的名字、無回應,再推他的肩膀——
那身軀自然而然往一側徐徐傾斜,直至撞上一旁的垃圾桶。
不戀慕。
山本武從冗雜繁複的夢中驚醒時,周身被乳白的窗簾籠罩在狹窄的空間里。
汗已浸透了衣服、床單。仰躺在陌生的床上僵楞一時,下意識去尋手臂的傷、觸到了凹凸不平的粗製布料。勉強串起的記憶里有雲雀恭彌的聲與影。
是對方送自己到了這裡。
牆上鐘的時針已越過三,深夜將臨破曉。
環視四周、病床旁的折叠椅支開著,有誰坐過的痕跡。掏了掏褲兜里,手機還在。
他猜想雲雀你或許沒有察覺、自己在那個下雨天偷偷存進你通訊簿的一串陌生號碼。手機草稿箱里,如同記錄心情的部落格一段段、擠滿了有關於你的文字。倘若他按下發送鍵,你會收到么。
打了幾個字、又全部刪掉,改成一句簡短的問候,發了過去。
——在做什麽?
過了許久,接不到對方的回覆,也是意料之中。
本打算今晚就這麼睡下吧,忽地,手機屏幕就亮了。
——睡覺。
他淺淺一笑。翻了個身、疼出滿身冷汗,所幸痛覺並非總是壞事。抬起手臂活動五指,雖伴隨著鑽心刺痛卻令人欣喜若狂,這隻手還活著。
——想見你。
房間里瀰漫著藥水揮發后鹹濕又刺鼻的氣味,在清冷的白露夜里蒸騰出一股燥熱。
抵抗著漫灌腦頂的昏眩,小武拔掉了輸液針頭,從床上掙扎爬了起來。
——不是剛見過了。
他抓起染有斑駁血跡的校服上衣、扶牆蹭出了病房。昏黃的檯燈下,身著白掛的中年男子伏在桌上打盹,他認得這人是夏馬爾。
——等我。
出於禮貌或許該打個照面,可大腦此刻出於什麽命令他要逃。並不打算驚醒夢中人,山本武一步一挪探到門口,推開虛掩的轉門悄悄溜了出去。
——你在哪兒?
夜風吹拂手臂的傷,從層層裹緊的紗布里、透出朵綻放開的殷紅。他漫遊在街上步履不穩像是醉了,路過一輛無客的士將它攔下、司機從後視鏡瞥了眼少年手臂上的傷口問,去哪兒。
儘管不要問,只要往前開。
這條路的盡頭,就是他的家。
——你家門外。
雲雀合上手機蓋,沉默了幾秒。
世界此時無聲,沒有人叩門,唯有男人的粗嘎喘息從鐵門那頭穿透進來。他匆忙從地上爬起來,腳沒停穩就猛地一滑、就跌跌撞撞地衝到玄關處,推開了門。
意料之中亦之外的少年正倚著墻,笑得狡黠。
「雲雀你,就不怕我是騙你的嗎?」
旋即,笑容就僵在臉上。
雲雀身上的白襯衫沾滿血痕,小武認出這和之前打鬥時所穿是同一件、左胸口印有并盛校徽。
「說是睡覺,卻連衣服都沒換呢。」
「廢話﹑」 雲雀斜眼瞪他、再轉身回屋裡,「我剛從你那兒回來。沒想到你小子這麼快…」
話音未落,就被對方用雙臂從後方結結實實地捆住。
一用力、好不容易才粘緊的傷口綻開了裂縫、溢出的血頃刻浸染了層疊的繃帶。凝視持續擴張的血印,雲雀無聲地將胸腔里已攢成團的紙張鋪展抹平,意外地反倒覺得、再發生也沒什麼。
兩個人杵在玄關,久無交流。
被摟到渾身滾燙又呼吸困難,察覺股間有什麽越發堅硬的物體抵著,雲雀才遲遲張口,「如果你想做,就去床上。」
「隨便我做什麽都行么。」
既然知道回答,你又何必問。
「恩。」
我只爲了聽你這聲回應。
窗外何時下起霧濛濛的雨。雲雀撐著幾乎散架的身體爬下床。
他坐在地上、從遍地雜亂中翻找自己的衣服吃力地往身上套,筋骨卻酸痛地不聽使喚。勉強穿得上長褲之後已經豁出一身虛汗,他驚喜從褲兜裡翻找到根擠壓變形卻完整存活的香煙,可四處尋覓不見打火機也只有作罷。
雨水衝不進窗裡,在玻璃上痛哭。
叼著未點火的煙,他蜷腿坐下側身依向床,頭耷拉在床沿。
視線的前方是微張嘴睡熟的山本武,腦海裡有關於昨夜正急速倒帶,那個人吸吮胸口時底氣不足地偷瞄自己的反應、托住自己身體循序漸進又迫不及待地闖了進來。
黑暗中的兩張被褥拼成一床、仰躺在中間的雲雀、雙腿被小武架在肩膀,在一擊擊推動之下無助地揪住枕頭一角。深知這屋子是獨層獨戶,於是痛並快樂時情不自禁地哼吟出聲也不會被第三人聽到,他才敢再放縱一些、再袒露一些。
傷口處迸發的血早已浸透了繃帶,順著男人堅實的手臂劃出一條血柱,冗雜著汗液一滴滴跌落在雲雀的臉上、唇邊、胸口,如同一場炙熱的雨。雲雀不由自主環緊那個人的頸、又鬼使神差般含住了眼前漲紅的耳垂,緊接著山本武便在這一舉動的催化下猛扎進來——
一股暖流浸潤了他。
兩個人維持著方才的姿勢抱著,待到胸口的躍動與喉間的呼吸沒再那麼嘈雜,山本武挪開肩膀、拖起對方高潮餘溫依舊漲紅的臉。
小武吻了吻他乾涸的唇,說,「雲雀,這一次你不是醉的。」
他的眼睛窄成一條縫,眉宇自笑。
我從未曾醉過。
山本武離開時,雲雀倚在頂樓窄小的陽臺。
罩著素色的襯衫,佇立在陰霾的天空下,他注視著少年的背影。
倘若兩個人的故事真的簡短到一句話便可以概括,那它句式的曲折一定像記憶會將彼此包裹起來。
如那時的場景,你回頭向我招手。我也伸出手,輕輕地揮動。
可終究隔著有些遠了,誰也辨不清彼此的五官,只是那隻手始終停不下來。用盡了全身力氣、所有的情緒,要笑著對你說再見。
如果再見這個詞代表告別回不去的時光。
那麼再見,我的少年。
全文終
